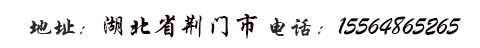龙出辽河源龙纹领路发现古代辽宁多彩文
|
白癜风的病因有哪些 https://m.39.net/disease/a_6701661.html 辽望·辽宁日报 提要 龙文化能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一个伟大民族产生巨大影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极其罕见。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龙的形象除了表达人们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强烈愿望外,还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中。龙纹在辽宁大地上留下清晰印记,考古工作者追寻这些印记,不断发现史料记载之外与辽宁有关的那些更加丰富、生动的往事。 喀左出土“蟠龙盖罍”:青铜器纹饰印证文字记载中的龙 进入有文字可考的时代,文字记载与出土文物相互印证,为人们描绘出龙的形象演变。 查海遗址陶片上发现的龙纹,可看作后世龙纹的源头。 赵宝沟文化陶尊器上的神兽纹,可见龙纹的雏形。 在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甲骨文中,仅古文字学家孙海波著录的“龙”字就有41个,反映了商王在重大活动中有“求龙”“向龙”“祝龙”等内容。 对于龙形象的描述,《荀子》中说龙像蜥蜴。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中记载:“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这样描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些文字描述了当时龙的各种形象。 辽宁省博物馆古代文物展厅里珍藏着一件镇馆之宝——青铜器“卷体夔纹蟠龙盖罍”,器身在灯光下泛出青幽的光,似在告诉人们,它已有岁了。 商周卷体夔纹蟠龙盖罍(上)及顶盖、肩部拓片(下),龙纹质朴粗犷。 这件文物的名称由三个意义组成。其中罍(读léi),是这件青铜器的用途,是商周时期贵族用的一种盛酒器。 “蟠龙”是指古代工匠精心铸造的一条龙。这条蟠龙盘踞于青铜盖上,有角,状如蜥蜴,似在随时发力跃起。在罍盖顶部、正对着龙的胸腹处,精巧地刻了几只蝉,是“一条吃蝉的龙”。 汉代瓦当上的蟠龙纹,龙的形象开始定型。 无论是文字记载还是传世文物都在反映一个基本事实,与流传到现代比较规范的、统一形象的龙不同,汉代以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群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创造龙。所以,这个时期的龙有的有爪,有的无爪,有的有翼,有的无翼。辽博藏的这件卷体夔纹蟠龙盖罍给人们展示的是商末周初龙的形象。 据辽博学术研究部馆员马卉介绍,出土于我省喀左北洞村的这件青铜器不是孤品。年,在四川省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窖藏中出土过一对蟠龙盖罍,它们与辽博收藏的蟠龙盖罍十分相似,只是辽博的这件腹部稍长,圈足稍矮,属于早期形制,即制作时间比那两件早一些,当为西周初年或稍早时间的青铜器。 马卉说:“包括这件罍在内的这些喀左青铜器窖藏的发现,对于研究周初的燕国历史有重要帮助。因为大量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周初燕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达了辽西地区。” 当然,卷体夔纹蟠龙盖罍带给人们的信息不止于此。文物名称中的第三层意思“卷体夔纹”是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最后确定下来的。年,这件文物出土时,专家认为器身上突目、利爪、尖齿的纹饰为“夔凤纹”,随着此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土的器物上有相同的夔龙纹饰,人们最终确认这种纹饰为夔龙纹,源自夏家店下层文化。当然,这种龙的形象不仅出现在青铜器上,还进入建筑设计当中,在辽宁大地上有序传承。 绥中秦行宫遗址:瓦当上的夔纹是红山龙纹变体 瓦子地,是葫芦岛市绥中县万家镇杨家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地名,这里出土了大量陶片和大瓦当。经考古确定,这里是秦行宫遗址。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大瓦当上有清晰的夔纹图案,可分为两种类型。数量较多的为高浮雕夔纹,与青铜器上的纹饰相比,夔龙已简化,呈蜷曲状,两厢对称,状如山峦,可以看到商周青铜器上夔纹的影子。最大一件被称为瓦当王,瓦面直径54厘米、高44厘米、厚2.5厘米,瓦身长78厘米,是迄今已发现的历代瓦当中最大者。同类的瓦当曾发现于秦始皇陵2号建筑基址,是秦代宫殿特用的建筑构件。 秦代夔纹大瓦当。夔纹用于建筑,其头部、身体皆简化、变形。 另一种夔纹瓦当数量较少,考古人员将其称为变形夔纹,头部、身体皆简化。 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华玉冰说:“从目前夔纹大瓦当的出土地点分析,秦代使用夔纹大瓦当的建筑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结合史料记载,秦代曾在这里祭祀海洋,宣誓与强化一统的帝国意识。” 夔,是龙萌芽时期的形象。《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夔,神魅也,如龙一足。”这些文字表述与古代器物上的夔纹相对应。 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夔龙纹是红山文化时期龙纹的变体,最早见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器物上,常见于商周时期。在商代,夔龙纹通常是以独立纹饰形式存在。西周时期,夔龙纹演变成弯曲、流畅的“S”形状。这一时期,夔龙纹与饕餮纹并用,互相影响,呈现质朴粗犷、神秘、狞厉的龙纹图案,强化了统治阶级的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诸子百家用理性解释世界。随着儒教和道教的盛行,文化艺术更多地反映现实生活,所以器物上描绘的多为卷龙纹,龙身蜷曲如蛇,富有张力,多以单独或连续的方法构图,展现出激越、动荡的时代特征。 随着时代的发展,隋唐时期的龙纹图案雍容、华贵,而宋代的龙纹典雅、洒脱,明代的龙纹精致而端庄,龙纹进入黄金时代。到了清代,龙纹精繁而华丽,多以云纹、海水相陪衬,龙翱翔于云海之间,称之为海水云龙纹。 研究认为,龙纹经历了一个从简洁、抽象到繁缛,从狰狞、严肃到活泼、生活化,从简单的动物崇拜到寓意丰富的吉祥纹样的演化脉络。而且,从汉代开始,龙形图案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专有,龙的形象基本定型,目前发现夔龙纹饰用于高等级建筑则是从秦开始。 朝阳“三燕”和龙宫遗址:成对雕刻的龙规范又严谨 从史料记载来看,以龙为名字的都城,非龙城莫属。那么,龙城在哪?研究者一直争论不休。 转机出现在年。这一年发生的大地震对朝阳市的北塔造成严重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省从年开始对朝阳北塔进行维修,历时10年。 正是在研究和维修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朝阳北塔下发现了高约7米、纵横约90米的大型夯土台基,在台基上面的建筑倒塌堆积层中出土了典型的“三燕”时期文物。 “三燕”是指魏晋南北朝时以慕容鲜卑贵族为主体先后建立的三个地方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前燕、后燕、北燕。“三燕”的统治时间前后相继持续了80多年。 三燕时期四神纹覆斗式柱础石,成对雕刻的龙纹规范又严谨。 《资治通鉴》中记载:“咸康七年辛丑(公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国内史阳裕等筑城于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立宗庙、宫阙,命曰龙城。”《晋书》中也记有:“(慕容皝)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 龙城的宫殿在哪?《晋书》中载,东晋永和元年(公元年)四月“时有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 大型夯土台基出土4个硕大的柱础石,长宽各达1.2米,分为四神纹覆斗式和双龙纹覆盆式两种样式。四神纹覆斗式柱础石的斜面及上面四角雕有龙、虎和朱雀等四神兽及云纹。四个侧面各雕有两条龙,龙头向外,龙尾向内,做反向奔跑状。双龙纹覆盆式柱础石共发现3件,覆盆部位浅浮雕两条龙,首尾相接,盘绕一周。龙身曲长,张口露齿,须发后拂,有飞翼。成对雕刻的龙规范又严谨。 金代铜镜上的双龙纹,龙的形象典雅、洒脱、精细。 龙纹的出土证实,这里就是和龙宫。朝阳市突出贡献专家、朝阳市北塔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董高说:“龙是中国特有的图腾,汉代以后,龙逐渐成为皇权的象征,龙纹成为皇家专用的装饰题材。”他指出,龙纹柱础石、规模宏大的夯土台基以及其他多种考古发现,帮助人们准确认定了朝阳古城区正是龙城所在地,后来修建的北塔,建在了和龙宫宫殿的基础之上。 几处龙泉成佳酿 “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汉书·食货志》中的这句话,道出了酒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而在中华传统酒文化中,龙的形象被广泛应用,龙与酒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沈阳有多个与酒有关的、带有龙字的地名。 例如,因相传曾是“涌龙泉”烧锅酒坊所在地,沈阳市和平区南湖街道龙泉路由此得名。而沈阳市沈河区龙凤寺巷以前曾被叫作官烧锅胡同,这一名字也与清代的烧锅酒坊有关。 当然,在沈阳,酒与龙字结合最紧密、最著名的当数老龙口。在当地人看来,老龙口这一地名已经与酒画上等号。这里有东北地区建造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连续烧酒时间最长的老窖池群。在历史上,因其位于清代盛京城的东门,而城东门又被称为“龙口”,因此得名“老龙口”。 清代,烧锅酒坊遍布沈阳。《清实录》记载:“今闻盛京地方,仍开烧锅。盛京口外‘蒙古’交界之处,内地人等,出口烧锅者甚多。”这里的口,指的是长城关口。造酒者选个好地点,搭起一口大锅,用当地产的粮食进行蒸馏,相对简单的工艺使得造酒利润丰厚,人人争而为之。 走过千年,中华酒文化醇香依旧。一家人,围桌而坐,举杯欢庆。此刻,酒是团圆,是祝福,更是期待——在新的一年,龙腾虎跃,龙凤呈祥,龙马精神…… 文心雕龙 矫若惊龙甘海民篆刻 矫若惊龙,像惊龙那样腾空飞舞,多形容书法灵动或舞姿矫健。《晋书·王羲之传》中有“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一句,称赞王羲之的书法飘逸得如同流动的云,矫健得像受惊的龙。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朱力伟解释,矫若惊龙的笔势或舞姿,非常人所拥有,其遒劲之力、刚健之姿、飘逸之态,让人叹为观止,这里面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视觉美感。 优秀的传统文化给现代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和丰富的精神滋养。国风吹起,文化大美,历史的文脉、民族的记忆活在当下,我们在浓浓墨香中书写,在悠悠长歌中舞动,尽显矫若惊龙之气韵,用文化自信营造出宏阔而悠远的气派。 勇毅、矫健中蕴含着柔美、飘逸,这是中国式的审美。人文精神和文化自信的交融,写就最美好的中国故事。在文化自信日益增强的时代背景下,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新篇章的行动中,我们更需赓续文化血脉,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活力,答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力量。 见习编辑:白复海 记者:郭平、谭硕、吴丹 责编:张艺凡审核:李德强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uichaoyanga.com/scyzz/11825.html
- 上一篇文章: 专业解答风水画旭日东升挂客厅真的好吗百
- 下一篇文章: 震撼照片见证烟台百年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