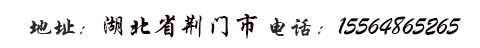游荡集在此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期盼朝阳下
|
立持的文字散发着遥远的旷野气息,让人想起鲍尔吉·原野笔下的星星——“夜海里泅渡的一群白象,白象们蹲在黑色的礁石上等待清风”。我们大多是在水泥森林的包围下成长、被精致的现代文明所俘虏的都市人。只有踏上荒漠、草原、山林的时候才能触及最原始而质朴的力量。自然以她迷人的危险、磅礴、辽阔,和永无止歇的生机呼唤着人类。 这篇散文记述了在甘南登山、露营、观日出的经历。而这三天两夜的冒险已经超越了冒险本身的意义。相比渲染攀登本身的艰辛体验,作者更愿一种传统的方式去描述身体与自然的交融感。草木、风、阳光,深夜的苦寒和黎明的颜色漫溢而出……在细腻之中显出壮阔与澎湃。“在此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期盼朝阳”,正如我们总会在无数个文明的困境中回头,向自然汲取汩汩的生命之泉。 甘南记行(下) 作者 立持 熄火,星空无比的灿烂。来自物理院,留着一头艺术气息浓重的长发的王公子开始教我们如何辨别星座和银河。 也许是上课打瞌睡的条件反射太过强大,我在帐篷里听着听着天文课便睡着了。我们扎营于山坳处,避风,但夜里冷空气之刺骨仍然无法躲避,每一次呼吸都感到此前凝结的空气突然像冰河冻解一样在我脸上流动。我在帐篷里做的梦,梦境都清晰明辨,而且梦里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也许只有这样深刻的梦才能勉强保护我的睡眠,不至于为寒冷所惊扰。 半夜我还是被冷醒。银光透过帐篷,把帐内的衣物映得清晰可辨。我以为黎明来了。往帐外探首,天空深蓝,一轮明月停在西山上。以往见到这样的月光,我一定满怀真挚的倾赏,矫情地做一点“像一个温润而光明的茧”之类的比喻,而此刻我只觉得它就是一座巨大而深沉的广寒宫,银光所照处,呵气成霜。古人之命名,诚不我欺。 月光里写满了黎明之到来的遥远。这种遥远的期待像心里缓慢融化的冰块,你能预感到它终会融尽,但每一秒都过得苦寒而漫长。我感到脸庞冷得麻木,像面具一样挂在头上,应该在月光中疲惫而苍白吧,忽然想起《呼兰河传》中的一句话,“满月入屋,漫天星光,人生为何,如此凄凉。”以前我读不明白为何满月可以衬托凄凉,当下才恍然大悟——它如此明亮,如此圆满,却不能制造丝毫温暖。 下半夜我在帐篷里冻成筛子,翻来覆去也找不到一个睡姿可以减弱寒冷的侵袭,只有掐紧拳头,就像拧紧湿润的毛巾能把水分挤出来一样,或许死死地紧掐拳头也能逼出手中的寒气呢?旁边的隋公子被吵醒,他从抓绒睡袋里探出头来,一摸我的睡袋,感叹一句,“唉,这么薄,没有野外生活的经验啊。”随即把他的羽绒服裹在我的腿上。但我还是冻得睡不着,于是他便很有牺牲精神地陪我聊天。 我说,原来以为在大山扎营,最可怕的是狼,结果,现在看来,在狼叼走我之前,冷空气就要把我吃了。 他说狼没什么可怕的,已经被人类教训得差不多了,现在大山里出没的多是独狼,也只敢欺负一下小羊羔,见到人类的房屋就躲得远远的。 我说,以后野营找夜里温暖的地方。 他说,这已经是他经历过的最温暖的地方了。“我们去年在扎尕那,夜里下大雪,把帐篷埋了一半;我们帐篷下湿漉漉的,泥土水分很足,想结冰,但被我们的体温烘得结不成。睡觉的时候转身就能听见底下水黏土的吧唧声。” 聊天似乎有取暖的功效,反正能把我哄得没那么在乎寒冷而入梦。 早上六点,山里依旧银光一片,只不过晨光代替了月光,而夜里月光匝地如霜处,便真正为白霜所覆盖。白天吸饱雨雪的鞋子,夜里放在帐篷外,清晨能敲出冰晶。我探头出帐篷,又缩了回来,妄想要等太阳出来才出帐篷。(在甘南山区,有无阳光的照射可以使气温相差二十五度)在帐篷里单手撑地,制造一点发力取暖的机会,一只手捧着电子书。看了一段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觉得作者在贡布雷的生活太温馨了,饮热茶,盖毛毯,还有佣人嘘寒问暖,直教瑟瑟发抖的我顾影自怜,不看了,换一个;读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读到《寒风吹彻》一篇,从气候的寒冷深入到人情的薄凉,似乎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之下,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乍看之下和此刻的我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但到底不想我周围的人像刘亮程预示的那样都在寒冷之中各自为战,况且隋公子对我一路关照有加。不看了,再换一个;读《里尔克诗歌选集》,从《鸟群从他身上钻过的那人》到《几乎是从万物向感觉示意》,有“空间从我们伸延并将事物翻改:使你得以感知一棵树的存在”之句,有“哦房屋,哦草坡,哦夕阳,突然间你几乎让它呈现”之句,嗯,很好,不明觉厉,就要诗歌这种模糊感,似乎它没说什么准确的话,却能替你倾吐一切糟糕的情绪。 早上在穿越帐篷的鼓励声中,男生起来,绕着帐篷跑圈,待手脚不再冷得麻木,便到山上更高处取泉水做早饭。太阳还未出来,我们急切地要生火,但柴草在晨霜的浸染下燃不起来。 黎明比半夜还冷,真是让人在最大的希望和最深的绝望之间踟蹰——寒冷让人想发疯似地打滚,饥渴又让人无力,但心想太阳马上就出来了,一切就要好起来了,便有种望梅止渴的坚挺。然而晨雾又让方位难辨,茫茫不知往哪里翘首以盼。 黎明时分的路况不甚明朗,加之晨霜削弱了路面的摩擦力,溯源而上的一行人像摸黑前进的小偷一样葸缩前行。我跟在有经验的人后面且行且期盼,只想着走向高处能更早地接触阳光。 在取泉水的地方,我们没有立即获得朝阳的青睐,却因为登高望远而看见远方的高山平原上一片拿坡里黄,心里的希望立即像一口气一样被提到了嗓子上,伴随着成倍地发酵的妒忌之情——我努力登高去接近朝阳,最后却眼巴巴地看着朝阳明媚在对面山头的人身上,虽然它始终会眷顾山的这一头,但却要等它走那么长的路,而我还无力去主动地缩短距离。而且在等待的期间,我亦无心眷顾其他的事情。于是我在能见到朝阳的地方来回踱步,像干渴的人等待深井里慢慢摇上来的一桶水,我直勾勾地盯着朝阳的足迹。它慢慢地织上这边的山尖,然后是山壁,最后才摇晃到我双足能跑到的灌木丛里。我立刻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向灌木丛,在披上霞光的那刻,感到人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就跟植物一样,要顺应自然的节奏,要向阳,什么“外出要涂防晒霜、打太阳伞”之类的观念通通抛诸脑后,只想痛快地呼号,就像看见黎明就打鸣的公鸡一样,宣泄生存的焦虑。 朝阳临照,周围的事物越发明朗,然后我才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uichaoyanga.com/scycd/5374.html
- 上一篇文章: 刚刚发布年度市级文明单位文明
- 下一篇文章: 海鲜来袭破冰而出,让我ldquo鲜